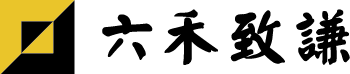投资中的历史观 | 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在那时?

编者注
对于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研究,无论在学术圈,还是大众传播领域,都是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个话题。我们曾推荐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及《西方将主宰多久》两本书,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议题做过精彩的论述。
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此的探讨,那就绕不开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于1998年出版的巨作《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兰德斯在此书中,批判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并将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和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合在一起,从历史出发,多层次地分析了财富创造、国家兴衰更替的根本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宏大框架下,兰德斯认为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小细节反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技术情况:眼镜的发明才使得精准测量成为可能,东亚人对筷子的使用使得他们对需要精细手工的行业得心应手等。
而在分析工业革命为什么会诞生在欧洲这个最核心议题时,兰德斯归纳了三个重要的原因:
1)由于地理因素而分裂,及宗教改革让欧洲可以获得进行学识探求的自主权。
2)欧洲在不断的发展中找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套方法论,如实证思维、数学化推理等。
3)科学发展的常规化,不同国家间科学家的定期交流、科学竞争等。
而正是这三个原因的存在,使得欧洲慢慢积累起科学思维及技术,直到突破了阈限,爆发了工业革命。
与戴维斯同龄的芒格也将此书列在其20本推荐书目之中。以下选自《国富国穷》第14章《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是在那时?》,祝开卷有益!
——麦考利《骚塞论社会》(1830)
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那个地区、那个时期?这确实是个双重的问题。
其一,一个国家为什么又怎么样冲破习惯和常规知识的甲壳而达成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呢?毕竟,历史也展现过别样的例证,说明机械化和无生命动力的应用并没有产生一场工业的革命。
在这一方面,大家可以想想宋代的中国(麻纺、冶铁),想想中世纪的欧洲(水力和风车技术),想想现代早期的意大利(捻丝、造船),想想“黄金时代”的荷兰。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后却发生在18世纪呢?
其二,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某个别的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呢?
这两个问题是一体的。回答其中之一则需要回答其中的另一个。这就是历史之道。
针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我想着重说明聚集(即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以及突破(即达到并且通过阈限)。我们已经说明了穆斯林和中国人的学识和技术进步所受到的阻碍。那不仅是改进的迟滞,而且是停顿的制度化。

图:戴维·兰德斯(1924-2013)
而在欧洲,情况却截然不同:我们具有连续不断的积累。诚然,在欧洲,如同在别的地方,由于政治的变故和个人的禀赋,科学和技术也有其坎坎坷坷,或强或弱的领域以及重心的转移。但是,如果必须指出关键的、富有欧洲特征的成功根源,那么,我想强调以下三点思考意见:
(1)越来越大的进行学识探求的自主权;
(2)以一种共同的、具有含蓄对抗性的方法的形式,在不统一中发展统一,亦即创造一种论证的语言,使其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得以确认、使用和理解;
(3)发明的发明,亦即研究的常规化及其传播。
自主权
争取学识自主的斗争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围绕传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所发生的冲突。当时,主宰欧洲的是罗马教会的观点,是由圣经规定的、由古人的智慧加以调和而不是加以修正的自然观。这种观念庞大多数定义表现在经院哲学中,因为这种哲学体系(包括自然哲学)造成了一种具有全权和权威的意识。
新的概念必然地以一种傲世的和潜在颠覆性的力量进入这个封闭的世界,一如它进入伊斯兰世界一样。但是在欧洲,由于新思想能得到实际应用,接受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受到了企图利用新颖事物使自己优于对手的统治者的保护。
因此,并非偶然,欧洲逐渐培养起对新生事物的崇尚和争取进步的意识。这是一种信念,它同崇尚先前优雅的怀古情节真实地摆在面前,相信当今的人们比过去更富裕、更聪明、更能干。
正如1306年乔达诺教士在比萨的一次布道中所说:“但并非所有的(技艺)都已经被发现;我们将永远看不到寻求它们的尽头……而新的技艺总是随时被发现。”
当然,陈旧的看法依然阴魂不散。但是在欧洲,教会的影响范围却受到了世俗当局的对抗性要求(凯撒对上帝)以及来自下层的在宗教信仰上持有异议的人所酝酿和聚集的火焰的限制。
这些异议教派或许在学识和科学方面还没有摆脱偏见,但是他们却破坏了僵死教条的一致性,从而暗地里促进了事物的新生。
对权威性最具摧毁力的是个人经验的扩展。例如,古人认为没有人能够居住在热带地区,因为那里太热。葡萄牙的航海者很快就证实了这种偏见的谬误。他们疾呼不要迷信古人,说“我们发现事情正好相反”。
加西亚·多尔塔的父母是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本人是个忠诚的但当然是隐瞒身份的犹太教徒。他曾在萨拉曼卡和里斯本学习医学和自然哲学,接着在1534年乘船到了果阿。
在果阿,他充当葡萄牙总督的医生。在欧洲时,他曾经受到教师们的恫吓,从来不敢怀疑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权威性。而现在,在葡属印度那种非经院气氛的环境中,他感到可以自由地睁开自己的眼睛了。
他写道:“对于我来说,一位目击者的证词,比起所有医生以及所有写出虚假信息的医学大师的言词更有价值,”并且还写道,“人们现在一天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比罗马人经过100年所知道的还要多。”
方法
仅仅观察是不够的。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必须理解并且作出并非幻术的解释。没有见过的事物,不能予以信任。因此,独角兽、蛇怪和火蛇就难以信其有。对于当年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用事物的“根本”性质去解释的现象,新的哲学都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事物存在于自然之中。
而且,从很早开始,这些探求者就渐渐认识到数学对于详细说明和系统表述观察结果具有巨大的价值。
为此,罗杰·培根曾于13世纪在牛津说:“一切范畴均决定于量的知识,而量的问题是由数学探讨的。因此,逻辑的全部力量取决于数学。”
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
这样一种方法开辟了通向有目的的实验的道路。不再是等待观望事物的发生,而是促使事物的发生。
新的方法是感知同计量、实证及数学化推理的有力的结合,这种新方法是获取新知识的关键。其实在的成就保证了不管后果如何它都会受到保护和鼓励。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像它一样获得发展。
如何进行实验则是另一个问题。人们首先必须创造研究策略以及观察和计量的仪器。等到这种方法在17世纪得到洋洋大观的进展而结出果实的时候,已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的时间。这并非意味着知识发展的停滞。这种新方法起初应用于天文和航海、机械和战法以及光学和测量等领域——它们都是一些实用事物。
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从伽利略开始,实验才变为一个系统。这不仅需要进行重复的和可重复的观察,而且需要深思熟虑的简化作为观察复杂事物的窗口。想要发现坠落物体的时间、速度和覆盖距离之间的关系吗?那就把这些物体从一个倾斜的平面上慢慢地滚动下来吧。
科学家必须进行更好的观察,而望远镜和显微镜一经发明(约在1600年),他们就能做到了,从而开辟了新的境界,其奇异和强大能够同早些时候的地理新发现相比。科学家们还需要更精确的计量,因为就一个指针来说,最小的移动都会造成天壤之别。
因此,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天文学和数学教授佩德罗·努涅斯在16世纪初叶,为了给航海和天文的读数提供一度的分数,发明了游标。这种游标后来改进为游标卡尺,随后又有千分尺的发明。
这种测微仪采用细金属丝进行判读,用螺杆(而不是滑尺)来达到精密控制。其结果是测量数据达到一毫米的1/10,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天文学精确度。(请注意:学习制造精密螺旋就是一项重大成就)
追求精密的同样努力还显示出时间计量的发展。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需要把事件的时间测定到分和秒,因此克里斯琴·惠更斯在1657年发明了摆式钟表,又在1675年发明了平衡游丝,使其成为可能。
此外,他们还需要效率更高的数学分析工具;他们从笛卡儿的分析几何学中,而且还进一步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中获得了这种工具。这些新的数学学科对实验和分析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常规化
西方科学的第三个机制性支柱是科学发现的常规化,即发明的发明。西方广泛分布着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工作在不同的国度,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却是一个共同体。
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
在17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1588—1648)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
最早的学术团体出现在意大利,即1603年罗马的猞猁科学院和1653年佛罗伦萨短暂的奇门托科学院。但是,从长远看,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北方学术团体:1660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1635年成立的巴黎学院以及其后继者成立于1666年的科学院。
甚至在此之前,非正式但却是定期在咖啡馆和沙龙里的聚会就曾经把人们和问题汇集在一起。正如梅森在1634年所说,“各学科彼此发誓要保证不可侵犯的友谊。”
当时,那是合作,但却由争夺威信和荣誉中的剧烈对抗而得到极大的加强。在16世纪那种学术团体的环境中,这种对抗常常采取的形式是隐匿不报、半露半含、拒绝发表、把精彩部分留作辩论和反驳。
一般说,声誉是对科学家的激励,而且即使在那个早期的年代,科学也曾经是一种领先的比赛。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的狂热爱好者,常常在环境优雅的沙龙里,展示并且宣讲自己的发明,变得如此重要;在座的女士和先生们于是成了这些成就的见证人。
而且,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包括业余的和专业的,会如此急切地创办学报并且使注明日期的文章得到发表,并且还要重复试验,证实结果,作出修正、改进,更上一层楼。
因此印刷机和活字的作用也变得至关重要;还有,拉丁文本来曾是各国专家学者中间进行国际交流的非常宝贵的手段,到了这时也改成能被更多公众理解的各国语言。再者,这样的传播工作和设施,没有一件能够在当时欧洲以外的地方出现。
科学的方法和知识在应用之中获得了收益,最重要的是在动力技术方面。在那几个世纪里,较老的动力装置,即风车和水轮,继续受到注意,效益有所提高;但是,伟大发明却是借助蒸汽把热能转换为功率。
没有别的任何技术比这更加依靠实验了。对真空和气压的探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开始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才通过几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而结出果实,他们是居里克(1602-1686)、托里切利(1608-1647)、玻意耳(1627—1691)以及帕潘(1647-1712),分别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
诚然,18世纪的科学家们没有能够说明蒸汽机为什么而且怎么样进行工作。做出这种说明尚需等待卡诺(1796-1832)和热力学定律的出现。然而,说蒸汽机成就于知识之前,并不是说这种机器的建造者没有吸收先前的科学探索成果,包括实质的成果和方法的成果。
瓦特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院长和导师布莱克并没有传授给他建造凝汽器的想法,但是跟布莱克一道工作却教会了他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践和方法。
即使在凝汽器这一点上,瓦特这位英雄的发明家也不是一人独占全部功劳。他是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一些教授的朋友,是英格兰一些杰出的自然哲学家的朋友,还是国外一些科学家的朋友。他钻研了数学,做过系统的实验,计算过蒸汽机的热效能。总之,他改进蒸汽机技术,是依靠了当时已积累的知识和理念。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
请让我举例说明。在14世纪的意大利,具有天赋的机械师们找到办法进行捻丝,就是利用机器梳纺整经,而且尤为感人的是他们是利用水力来驱动这种装置。在这种技能的基础上,意大利的丝纺业繁荣了好几个世纪,引起别的国家的妒羡。
法国人在1670年揭开了这个秘密,大约在同一时期荷兰人也学到了手。在1716年,托马斯·隆比经过数年耐心的侦察之后,终于把这种技术带到了英格兰并且建立起一座大型的水力厂房,雇用了数百人。
那是一座工厂,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能同后来的棉纺厂相比。说它“几乎”,是因为其差别在于:隆比的丝纺厂,加上先于它而建立的手工捻丝作坊以及一些较小型的模仿机器作坊,在生产规模上超出了英国对于丝纱的需求。因为丝毕竟是一种昂贵的原料,丝制品所供应的只是少数富裕的顾客。
所以,隆比的丝纺厂比18世纪70年代第一批棉纺厂早半个世纪建立,却没有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典型。人们未能从丝纺中获得某种工业革命。
羊毛和棉花则另当别论。当时,羊毛打个喷嚏,整个欧洲就会患感冒;要是棉花打个喷嚏,全世界都会难受。羊毛在欧洲尤为重要,而棉花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从某些方面来说则属偶然。
棉纺是个朝气蓬勃的新生儿,它比起中世纪就建立起来的那些古老的毛纺和麻纺部门在规模上依然小得多。制造精纺机械的最初企图是以羊毛为目标的,因为羊毛精纺有利可图。但是,当羊毛纤维证明不易梳理而棉花却能随意摆布的时候,发明家们便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这种较容易驾驭的材料。
还有,羊毛手工业积习太深,其从业大军有着既得利益,这就妨碍了变革。而棉纺业成长迅速,录用新的人手,感到实行新的方式比较容易得心应手。技术革新过程总有这种情形:教新手学新招比起教老手练新把式要容易得多。
为什么机械化有利可图呢?主要是因为纺织工业的发展已开始超越劳动力的供应。英格兰已经跃进到使用农村的手工制造力量,但是这种包工的活动很分散,要翻山越岭,分活再收活,把成本逼了上去。
同时,雇主们为了竭力满足需求,提高了工资,就是说,他们增加了为自己的成品所付出的成本费用。但是,令他们沮丧的是,更高的收入只使得工人们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而提供的工作量却实际上减少了。
制造商们感到自己在踏空车——白费劲。他们违心地希望食物价格上扬。生活费用的上涨或许能迫使纺纱工和织布工多卖力干活。
然而,工人们确实对市场刺激做出了反应。他们是工资劳动者,也是承包人。这种双重身份向他们提供了在损害作为发包人的手工业业主的情况下自我致富的机会。
纺纱工和织布工往往从一个商人那里拿到原料,然后把制成的物品卖给竞争者,时而搪塞一人,进而搪塞另一人,把自己的契约玩耍得滴水不漏。他们还学会扣留出一些原材料供自己使用:由于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决不会出现反向的供应曲线。
织布工为了尽力掩盖这种盗用行为,就减少织物的厚度,降低其质量,用假货或添加物加以充塞。而制造商则反过来严格检验每一件产品而且必要时“扣减”成品的价格,企图用这种办法来阻止这种盗窃行为。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雇主和雇员之间代价高昂的冷战。
制造商们吵吵嚷嚷,要求民事当局给予帮助。他们要求享有对怠工者和赖账者施加体罚的权利(对这些人罚款是无济于事的),享有未经准许进入织工庭院搜查被盗原料的权利。这些要求毫无结果,因为对一个英国人来说,家就是他的城堡,神圣之至。
因此,不足为奇,沮丧的制造商们转而考虑要建立大型的工场作坊,因为在那里,纺织工们必须准时到达,全天在监督下工作。这绝非区区小事。对于商人兼制造主来说,庭院手工业毕竟具有巨大的优点,特别是开办费低廉,一般管理费用低廉。
借助这种生产方式,提供厂房和设备的是工人,而且一旦业务下降,发包人只需辞去订单就可以了。而另一方面,大型工场或作坊则需要注入大批资本:首先是土地和厂房,外加机器设备。
此外,发包式的手工生产受到每一个人的欢迎。工人们喜欢摆脱纪律的约束,喜欢享有随心所欲地停机离开的特权。工作的节奏反映出这种自主性。典型的是织布工人,他们长时间歇着玩着,混上大半个礼拜,然后快到周末时,为了在礼拜六交货领取工资才最后努力工作。
产业内部的这种冲突必然导致工人们最终集合在一起,在监视和监督下劳动。不过,制造商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出钱来说服人们走出庭院进入工场。只要工场里的设备同家庭中的设备一样,工场生产的成本就要高。
因而,在纺织业中为集中劳力所做的努力,虽然在英格兰可以上溯到16世纪,却一律失败了。在欧洲,情况则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各国政府资助劳力并将他们分配到大型的手工作坊——“制造工厂”或是“原始工厂”,企图用这种方法来促进工业发展。但是,这是一种人为的繁荣,政府的支持一经撤销就招致了破产。
工厂具有竞争力,是在使用动力机械之后。动力使得驱动更大型的、更有效能的机器成为可能,从而使产品价格以越来越大的幅度低于庭院产品。手工纺纱工迅速消失了;手工织布工消失得慢一些,但消失也是肯定无疑的。
尽管工人工资高一些,但对于守旧派来说,工厂依然像是监狱。那么,早期的工厂主是从哪里寻求到他们的劳动力呢?除了从那些不能够说不的人中间以外,他们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找到工人呢?
在英格兰,这就意味着往往是贫民院招募(买来)的儿童,还有妇女,尤其是年轻的未婚妇女。在欧洲大陆上,制造商们能够通过谈判利用囚犯劳力和军人。
这样就诞生了卡尔·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它是机器和动力结合的果实,也是动力(力和能)和势力(政治上的力)结合的果实。